英特爾汽車夢碎,蘋果、高通、華為各顯神通
作者:
AO記者 陳秀娟
2025-08-13 0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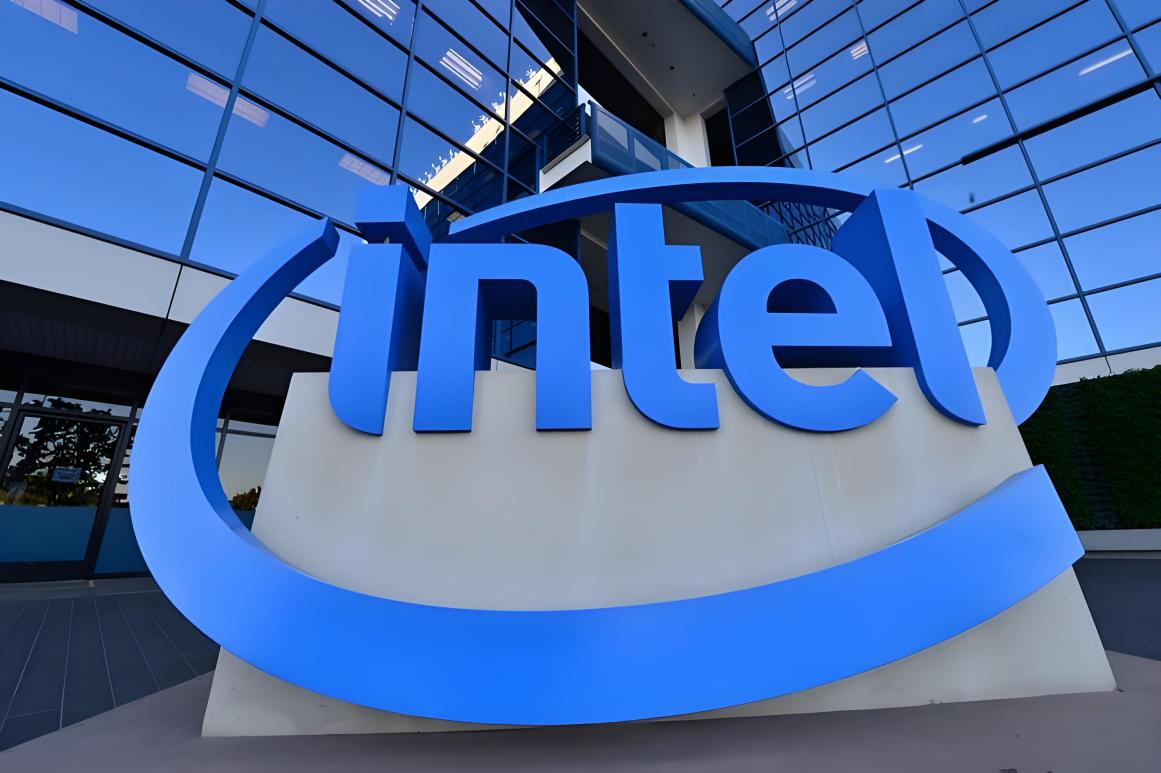
近日,英特爾宣布:將逐步關閉客戶端計算事業部旗下的汽車業務單元,并裁撤該領域絕大多數員工。這是英特爾在持續虧損壓力下,作出的艱難抉擇。
在此之前,英特爾新任CEO陳立武已向員工預警即將到來的大規模裁員。隨著“瘦身計劃”持續推進,英特爾的制造部門已啟動裁員,營銷部門也被整體外包。這個曾被寄予厚望的汽車業務,最終成為英特爾戰略收縮的第一個犧牲品。
現金流壓垮英特爾的汽車夢
2017年,英特爾豪擲153億美元收購Mobileye,創下當時半導體行業最大并購紀錄。Mobileye手握EyeQ系列視覺芯片、高精地圖與自動駕駛算法,被視為通往L3以上自動駕駛的“黃金門票”。英特爾希望復制當年在PC領域捆綁Windows的打法,把x86架構的計算平臺塞進每一輛車的后備廂,讓“Intel Inside”從電腦貼紙變成前格柵標志。?
然而,汽車產業鏈的復雜程度遠超英特爾的經驗值。車企對功能安全的認證需要三到五年,每一次軟件OTA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測試;而消費電子級別的迭代速度在車載場景里被大幅拖慢。英特爾擅長的高性能、高功耗、高價格方案,在電池成本敏感、散熱空間局促的車內環境里顯得格格不入。更棘手的是,Mobileye堅持“黑箱”交付,與英特爾設想的開放生態背道而馳。
2022年10月,Mobileye獨立上市,英特爾雖保留多數股權,卻放棄了將Mobileye技術與自家x86平臺深度融合的嘗試。不過英特爾并未就此離場,而是掉轉船頭押注“軟件定義汽車”。

在2024年CES上,英特爾發布AI增強型軟件定義汽車SoC(系統級芯片);2025年4月上海車展,其又帶來第二代AI座艙芯片。此外,英特爾將慕尼黑團隊擴充至500人,并在上海組建整車客戶支持團隊。
然而,這些舉措無法立刻轉化為營收。財報顯示,2025年第二季度,英特爾營收達129億美元,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然而,毛利率卻從去年同期的35.4% 驟降至27.5%,下降了7.9個百分點,凈虧損擴大至29億美元。
當現金流成為生死線,任何無法迅速自我造血的業務都變成了包袱。汽車芯片研發周期長、認證門檻高、客戶切換成本大,在財務模型里被標成“高投入、慢產出”的標簽,它自然成了英特爾“瘦身計劃”中最先被砍掉的包袱。
蘋果們的棋局仍在繼續
放眼全行業,英特爾的撤退并不是汽車智能化賽道的第一次“巨頭翻車”。例如,2016年,蘋果“泰坦計劃”裁員數百人;2022年,谷歌Waymo叫停自動駕駛卡車項目。然而,同樣是戰略收縮,蘋果們卻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徑。
2025年6月,蘋果發布CarOS 2.0,宣布與奔馳、路虎、保時捷共同定義下一代智能座艙交互標準,CarPlay徹底接管車內所有屏幕與算力。蘋果沒有造整車,卻用操作系統把整車靈魂攥在手里。?

從商業模式來看,蘋果賣的不是芯片,而是生態。每輛搭載CarOS的車都要向蘋果支付費用,并按照應用商店流水進行一定比例的分成。這讓蘋果在汽車業務上擁有足夠的耐心:硬件可以不賺錢,甚至前期補貼,只要用戶規模足夠大,后續軟件和服務收入就能覆蓋成本。
若把蘋果比作生態派,高通則是方案派的代表。2021年,高通以45億美元收購Veoneer的Arriver軟件業務,補全了從座艙到ADAS的端到端能力。高通把智能手機時代的“一站式整體解決方案”平移到汽車,即一顆SoC附帶BSP(主板支持包)、Hypervisor(虛擬機監控器)、中間件、參考設計,車企拿到手即可量產。這種模式讓高通在2024年拿下全球智能座艙芯片約60%市場份額。
反觀英特爾,其在汽車芯片業務上,試圖推出標準化芯片產品以降低成本、提高通用性,便于大規模生產和銷售;同時,又希望通過保留部分知識產權,讓車企能夠根據自身需求進行一定程度的定制化開發,打造差異化產品。但實際操作中,對于成本敏感、追求性價比的中國車企而言,英特爾的芯片產品價格相對較高,增加了整車成本壓力;而對于注重產品差異化、期望深度參與芯片開發的歐洲車企,英特爾保留部分知識產權的做法限制了他們對芯片進行深度定制的自由度,使其感覺產品過于封閉,難以滿足自身多樣化需求。
?
華為則為行業帶來了第三種發展模式。2023年,華為車BU獨立為智能汽車解決方案事業部,內部采用集成產品開發模式,把芯片、OS、算法、云服務打包成“全家桶”,先用在問界、智界車型上跑通商業模式,再向外部車企輸出。數據顯示,2024年,華為車BU收入突破263.5億元,同比增長約474%,毛利率高達55.4%,且實現年度盈利。?
相比之下,英特爾由于沒有終端品牌,也缺乏對整車定義的話語權,只能作為Tier 2站在價值鏈最末端,一旦主機廠壓縮成本,最先被擠壓的就是Tier 2的利潤。?
有分析認為,英特爾與蘋果、高通、華為等科技巨頭更深層次的差異在組織文化上。蘋果、高通、華為都把汽車業務上升為公司級戰略,CEO親自站臺,預算獨立核算;而英特爾汽車業務長期被放在客戶端計算事業部之下,與PC、IoT(物聯網)共用一條匯報線。PC團隊習慣了“一年一代酷睿”,汽車團隊卻需要“幾年一代平臺”;PC團隊把45% 毛利率視為底線,汽車團隊為了拿項目可以接受25% 毛利。文化沖突的結果導致汽車團隊在內部預算爭奪戰中屢屢失去話語權,這也導致研發投入始終低于競爭對手。
寫在最后:
回到英特爾自身,關閉汽車業務并不意味著徹底放棄出行賽道。Mobileye仍在獨立運營,EyeQ6H芯片將在2026年上車寶馬車型;英特爾代工業務獲得美國國防部3nm安全芯片訂單;數據中心“獵鷹海岸” GPU也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在AI訓練市場分食英偉達的蛋糕。根據規劃,未來英特爾將聚焦三大核心領域:高性能CPU、數據中心GPU、代工服務,其余業務要么盈利,要么剝離。?
然而,市場留給英特爾的時間窗口并不寬裕。在PC市場,AMD(超威半導體)憑借Zen 5架構持續蠶食份額;在數據中心市場,英偉達Grace CPU與AMD EPYC(霄龍)形成夾擊;在代工領域,三星、臺積電已經量產2nm。汽車業務的撤退,雖能為英特爾在2025年下半年節省約5億美元運營費用,但其失去的卻是一張通往未來十年最大增量市場的船票。?
汽車芯片的競爭終局或許不是“誰取代了誰”,而是分層共存:英偉達、高通占據高算力金字塔尖;華為、地平線在中端市場提供國產化替代;Mobileye繼續深耕L2 + 視覺方案。而英特爾,則可能成為那個曾經來過卻最終錯過的名字。

